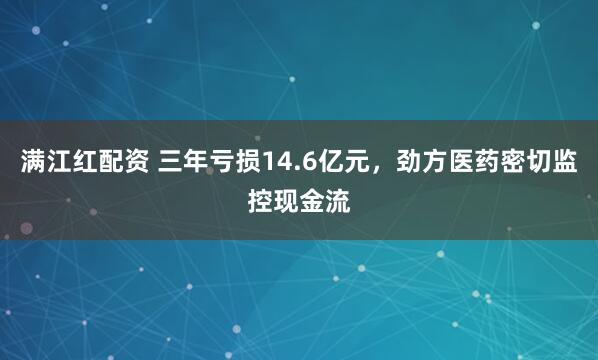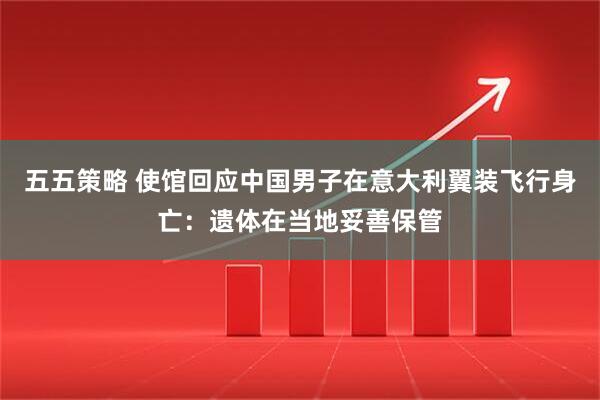牛鑫所
牛鑫所
晚霞下的潮州广济桥。视觉中国供图
韩江水悠悠流淌,环抱着粤东潮州这座古韵悠长的历史文化名城。它宛如一部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岁月的沧桑与文化的辉煌;又似一首悠扬的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历史的脉搏与诗意的灵动。从唐宋贬谪文人的悲歌,到明清雅士的浅吟低唱;从林大钦状元才情的尽情抒发,到历代文人墨客的墨香留痕,潮州在古诗的璀璨星河中,绽放出跨越千年的独特华彩。
韩愈开篇的文化序章
唐元和十四年的春日,本应是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时节,然而对于韩愈而言,却是一场命运的寒冬。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悲愤地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政治上的失意如同一记重锤,将他从繁华的京城长安砸向了偏远的国角潮州。在被贬的途中经粤北韶州乐昌,他于《泷吏》诗里与泷吏对话,“官今行自到,那遽妄问为”的诘问,以及泷官告诉他潮州“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此情此景,年逾半百的韩愈萌生了对自己未知命运的忐忑与赴任目的地恶劣生存环境的迷茫。
初至潮州,眼前“海气昏昏水拍天”的荒凉景象,让他的内心充满了失落与无奈。在《宿曾江口示孙湘》中,他发出“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的慨叹,星斗高悬,却照不亮他前行的道路,仿佛置身于茫茫的黑暗之中,找不到方向。
然而,韩愈并未被命运打倒,他以“八月治潮万古名”的担当,迅速投入到潮州的建设中。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他详细记录下“除复鳄鱼,安民惠工”的政绩。他亲植的橡木在笔架山韩祠前蓊郁千年,清代诗人郑兰枝在《韩祠橡木》中以“根深八月蟠祠古,叶毓双旌度岁寒”的诗句,生动描绘出橡木的古老与坚韧。这株古树,不仅见证了潮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成为了科举吉兆的象征,在月光下绽放出璀璨的光芒。韩愈的到来,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了潮州这片干涸的土地,开启了潮州文化开化的崭新篇章。
林大钦诗中的潮州画卷牛鑫所
明代才子林大钦,这位潮州古代唯一文状元,以其卓越的才华和独特的视角,为潮州文化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诗词,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潮州的文化星河中,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在他存世的诗词中,对潮州的自然景观有着细腻而动人的描绘。在《夏日吟》里,“天地何太郁,永日毒人肠。予怀良不恶,潇洒顺时芳。好鸟鸣深枝,茂林延疏光。薰风来平陆,杳然虚怀凉”,夏日的潮州,天地间闷热郁积,仿佛被一层无形的枷锁所束缚。然而,诗人却能在自然中寻得潇洒之态,深枝间传来好鸟的鸣叫声,如同天籁之音,驱散了心中的烦闷;茂密的树林透进稀疏的阳光,如同点点星辰,给人带来一丝希望;平陆吹来的薰风,带着丝丝凉意,让诗人的心怀也变得清凉起来。这首诗,生动地展现了潮州夏日自然的生机与活力,以及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
“白日照园林,春芳伤人心。及辰谐兹游,水石共追寻。和风澄暄景,鲜云垂薄阴。游鱼在清波,好鸟鸣高岑”,描绘出一幅如诗如画的春日潮州园林美景图。白色的日光洒在园林中,春天的芬芳却勾起了诗人别样的情思。他趁着这美好的时光去游玩,追寻着水中的石头。柔和的风让景色更加澄澈,洁白的云朵投下淡淡的阴影。清波中鱼儿自由自在地游动,高岑上鸟儿欢快地鸣唱。这首诗,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那份春日的惬意与宁静。
林大钦的诗词不仅描绘自然,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感悟。《夏日吟》中“静里乾坤胜,壶中日月长。卧龙终寂寞,跃马空腾骧。流连风景换,淹泊获吾常。世路今炎热,故山安可忘”,诗人在宁静中感受乾坤的美妙,在饮酒间体会时光的悠长。他联想到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即便如卧龙般有才华,最终也难免寂寞;策马奔腾之人,也不过是一场空忙。时光流转,风景变换,诗人在这漂泊之中找到了自己的常态。面对世路的炎热,他更不忘故山,表达了对家乡潮州的深深眷恋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春游篇》中“吾志在玄初,穷通祇自任”,则体现了诗人的人生志向。他的志向在于探寻事物的本源,对于人生的穷困与通达,都能坦然面对,展现出一种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感悟与潮州的文化传承息息相关,潮州文化中一直有着对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林大钦的诗词正是这种文化内涵的生动体现。
广济桥的诗学回响
“湘桥春涨水迢迢,十八梭船锁画桥”,郑兰枝笔下的广济桥在春汛中化作流动的长虹,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韩江之上,气势磅礴。这座始建于宋代的“梁舟结合”古桥牛鑫所,承载着无数诗人的才情与想象,成为了潮州文化的重要象征。
清代诗人杨淞在《腊月自汕头还家》里写道“凝阴催暝早,流水送年忙”,广济桥在暮色与流水的交织中,成为了时光流转的见证者。当暮色渐渐浸染江面,杨世勋在《韩江夜溯》中捕捉到“明月一轮帆照影,碧山千桁树濛烟”的绝美瞬间,桥影与帆影在江天交界处交织成一幅如梦如幻的水墨画卷。月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帆影在水中摇曳,仿佛是一群翩翩起舞的精灵;碧山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
桥东的“民不能忘”牌坊下,清代潮州知府吴均投官帽祭水的传说仍在流传。这位知府在洪水中的决绝一掷,体现了他对百姓的关爱和担当。郑兰枝在《龙湫宝塔》中写下“帆藏灯影三更月,缆系钟声五夜游”,宝塔的倒影与星月同沉,钟声在夜空中回荡,见证着官民共济的永恒瞬间。而林大钦若身处此景,想必也会以他的才情,为这桥、这水、这情,留下动人的诗篇,让广济桥的故事在诗韵中得以延续。
风物人文的诗意交融
凤凰洲的秋雨在郑兰枝笔下化作“云锁湘桥疑海市,烟迷笔岭忆蓬莱”的迷离仙境。当“凤凰时雨”的奇观降临,整个凤凰洲仿佛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云雾缭绕,如梦如幻。明末抗清官员、潮州七贤之一的郭之奇在《孟冬五日晤璞山上人》中以“寒菊终留秋后色,霜枫久醉日余曛”的意象,将自然气象升华为哲学思考。寒菊在秋霜中依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霜枫在夕阳的余晖中醉得通红,它们象征着生命的坚韧和不屈,让人在欣赏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人生的哲理。
这种对自然与人文的深度交融在明万历进士林熙春的《初冬邀张元辉萧彦得登新塔》里达到巅峰,“呼卢华表江风发,返棹孤城夜色开”的豪迈,让地理景观与人文情怀完美交融。诗人在新塔上与友人呼卢(一种赌博游戏),江风扑面而来,带来丝丝寒意;返棹时,孤城的夜色渐渐展开,仿佛一幅巨大的画卷。这幅画面中,既有自然的壮美,又有人文的情趣,让人陶醉其中。
潮州诗人对自然时序的敏锐捕捉,在明嘉靖廉吏王天性的《冬日即事》中呈现为“柳垂故叶仍存绿,桃剩残枝已著红”的细腻观察。冬日的柳树依然垂着绿色的叶子,虽然有些枯黄,但依然蕴含着生机;桃树的残枝上已经绽放出红色的花朵,仿佛在向人们宣告着春天的到来。这种对生命律动的诗性记录,让潮州的四季更迭超越了物理时空,成为永恒的审美对象。林大钦的诗词同样如此,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才情,将潮州的自然与人文紧密相连,让每一处景色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橡荫禅心的诗性见证
叩齿庵的晨钟里,韩愈与大颠和尚的会面被清代诗人、书法家陈方平写入《暮冬道上即景》:“日色分柑树,涛声起蔗林。”这一场跨越身份和信仰的对话,体现了潮州文化的包容与开放。当郑兰枝在《北阁佛灯》中描绘“玄天阁黄瓦红墙,重檐翘角”的景象时,这座见证佛道交融的建筑,已然成为文化包容的象征。玄天阁的黄瓦红墙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重檐翘角如同展翅欲飞的雄鹰,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开元寺的碧桃花在黄遵宪的《夜宿潮州城下》中“九曲潮江水,遥通海外天”的视野里,与唐代石幢的经文共同诉说着千年传承。九曲的韩江水奔腾不息,仿佛是历史的长河,流淌着潮州的文化记忆;开元寺的碧桃花在春风中绽放,如同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人们的心灵;唐代石幢的经文历经岁月的洗礼,依然清晰可见,它们是潮州文化的瑰宝,见证了潮州佛教的繁荣与发展。
这种文化融合在清道光梧州通判饶宗韶的《韩江感旧》中呈现为“桥水深深落凤台,当年风景已成灰”的沧桑感怀。桥下的江水深深流淌,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凤凰台上的风景已经物是人非,只留下岁月的痕迹。当清代潮州书法家杨洪简在《湘桥春涨》写下“仙人何处遇,桥影一桁疏”,那些消逝在岁月深处的历史片段,又在诗赋的缝隙中重新显影。林大钦的五律也融入了这种文化融合的大潮,他既受到潮州本土文化的熏陶,又吸收了当时盛行的王阳明学说等思想,其作品体现了潮州文化在多元交融中的独特魅力。

作者:谢岳雄
来源:南方农村报
富灯网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